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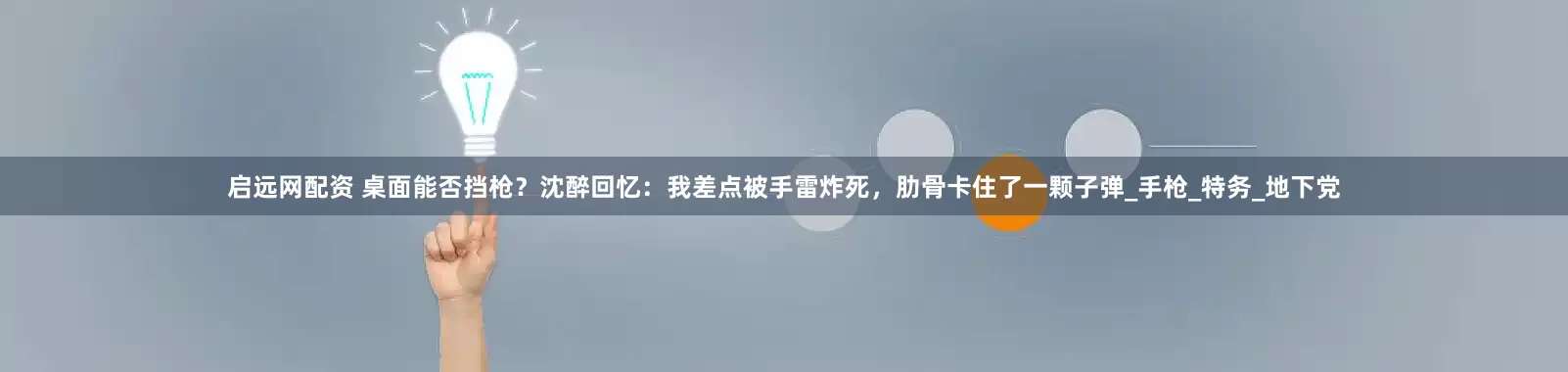
在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“神剧”中,总是能看到这样的场景:枪火四射、硝烟弥漫的激烈战斗中,绝望的枪手无处可躲,猛地掀翻一张桌子,或者抓起一把椅子,迅速将它们作为掩体,继续死命开火。屏幕上的人物似乎轻松应对,周围的飞溅子弹和激烈战况似乎都不在话下。每每见到这种情节,很多观众都会发出一声轻笑,认为这不过是编剧为了增加戏剧性而有意夸张的设定。
然而,作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山区的我,面对这一幕却并没有笑出声。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家里的那张松木桌面和黑桦木椅子。我不禁在心中默算:若是遭遇枪林弹雨,这些简陋的家具能挡住几轮子弹呢?
最近,翻阅了沈醉将军的回忆录,更是加深了我的这种思索。这位曾是原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老特务,在他的回忆中曾提到过一个令人唏嘘的细节:他曾在战斗中,两根肋骨卡住了一颗子弹。沈醉这番话不禁让人捧腹,却也充满了某种难以言喻的遗憾——这颗子弹,居然没有进一步穿透。让人不禁感叹,为什么子弹没有继续深入,突破这两根肋骨,造成致命伤害呢?
展开剩余79%沈醉肯定深知,自己曾在战场上与子弹擦肩而过的滋味。可他的回忆录却给了我们一个稍显可笑的意外结局:这颗手枪子弹没有完全穿透他的胸膛,而是卡在了肋骨之间,留下一道疤痕。这种情况让人疑惑:手枪的威力到底有多小?我们常见影视剧中,士兵们常常用手枪与敌方的步枪、机枪对射,看起来两者似乎没有太大差别,那么,手枪的实际威力究竟如何呢?
当然,这种步枪与手枪对射的场景,更多是停留在影视作品中,现实中的战斗可不那么简单。就像沈醉这样的军统特务,他几乎不会亲自持长枪上阵,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过他有使用长枪的经历。那么,他到底是怎样在地下党的枪火下,侥幸逃过死神的追击呢?
沈醉,作为戴笠亲自培养的特务,凭借过人的胆略与谋略,逐步从一个冷酷的杀手升迁为军统少将,后来甚至被提升为中将。这样一位深得戴笠宠信的特务,手上自然不会少有鲜血。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自己在“战犯管理所”的十年岁月,这一段历史无疑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尽管他最终获得了“起义将领”的认证,但那张特赦令始终是他珍视的无价之宝。
沈醉这位被称为军统“四大杀手”之一的特务,其实也并非无往不利。在战场上,他几乎以行刺、暗杀和逮捕为主,而这些任务也让他屡次险些丧命。他曾和吴敬中一起在军统的特训班担任教官,吴敬中教授情报与电讯,而沈醉则专注于“行动术”,即捕捉与暗杀的技巧。他的授课内容涉及了如何使用手枪、短刀、毒刀以及追捕与逃脱技巧。戴笠对沈醉的信任可见一斑,派他担任保卫凯申总统的任务,更是将其视作得力干将。
然而,沈醉虽然在军统内风光无限,但与周公和克公领导的红色特工相比,还是差了一些底气。特别是在他年少时,曾遭遇过一场令人羞愧的意外伤害:一次抓捕任务中,沈醉带领七八个持枪的特务去捉拿一对地下党夫妇,期间遭遇了地下党妻子的反击,被她用木棍击中左脚,导致终身残疾。回忆起那段往事,沈醉在《我这三十年》中写道:“这是我不光彩的伤痕,是革命同志给予的惩罚。” 他承认,这些伤痕都是他在执行任务时与革命者搏斗时留下的。
这段回忆也让我们明白,在特务的世界里,成功的案例远没有失败来得多。即便是沈醉这样的军统少将,抓捕地下党时也总是屡屡吃瘪。甚至有两次,沈醉差点命丧在地下党人的手雷和手枪下。比如1935年的冬天,沈醉和两个手下去抓捕一名地下党员,结果却差点全军覆没。那个地下党并不慌乱,冷静应对,并在最后掏出一颗手雷,威胁三人“动一动,大家同归于尽”。眼看局势一触即发,沈醉等人只得虚假笑脸,尽力化解危机。
尽管沈醉一度因敌人的威胁而陷入险境,但他依旧能凭借自己过人的冷静和智慧,化险为夷。在一次与地下党徒的对峙中,他在胸口中了一枪,但因距离较远,子弹没有完全穿透他的胸膛。那时他低头看到自己血流不止,依旧坚强地捂住伤口,避免血液洒在衣物上。当他被手下送到医院时,才发现那颗子弹卡在了两根肋骨之间。
回想起这些经历,我也不禁想起自己曾在靶场的体验。虽然我对枪械的了解不深,但也曾试过在靶场上射击。每当我完成一轮八一大杠的射击训练,肩膀的剧痛就提醒我,打仗不仅仅是智力的比拼,更是一场体力的较量。步枪的后坐力极大,每开一枪就如同挨了一记重拳。而手枪则相对轻松得多,射击时几乎感觉不到太大的反冲,射击的精准度也差距明显。即便如此,手枪依旧是致命的武器。而沈醉的遭遇,也使我不禁陷入深思:究竟手枪的穿透力有多强?如果换作其他型号的手枪,沈醉是否能够安然无恙?
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明确答案,但从沈醉的经历来看,无论是桌面、椅背还是其他任何临时做出的掩体,都可能在极端情况下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至于手枪的穿透力,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真正的答案,只能在历史的阴影中,继续寻找那些未解的谜团。
发布于:天津市广盛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